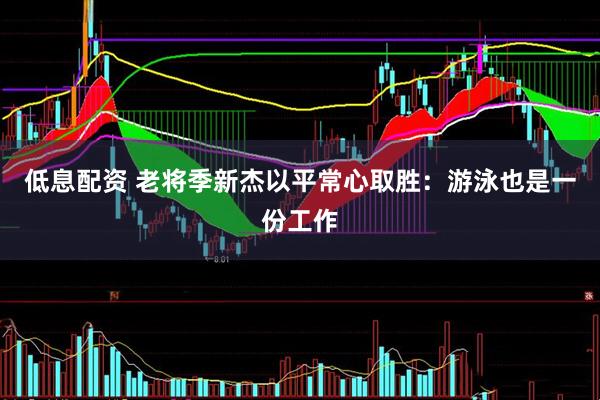1948年11月10日低息配资,华东野战军基本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。
就在这个关键时刻,刚从东北回到徐州的杜聿明提出了一个计划:让李弥兵团坚守徐州,邱清泉和孙元良兵团则从徐州南下,与中原的黄维兵团配合,先集中兵力打掉中原野战军(简称“中野”),然后再折回北上,解黄百韬之围。杜聿明的逻辑很清楚——面对解放军,必须先集中力量击破一路,否则就会到处挨打,完全陷入被动。
然而,在国军内部,像杜聿明这样“敢于进取”的将领已经不多。李弥不愿意独自留守徐州;总司令刘峙也不想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去放弃黄百韬,但更不敢把徐州置于险境——因为一旦徐州失守,他的地位也就不保。最终,杜聿明的方案被否定,蒋介石在南京拍板:
展开剩余79%- 黄百韬坚守碾庄;
- 邱清泉和李弥的一部分兵力向东增援;
- 李弥主力继续守徐州;
- 孙元良则掩护徐州的侧翼;
- 同时,中原的黄维兵团北调,会同李延年、刘汝明兵团向徐州靠拢。
这样一来,国军在徐淮一带集中了7个兵团,这是整个解放战争中他们最大规模的一次兵力集结。
但从战略上看,这种打法并无新意,几乎是老调重弹:哪支部队被围困,就固守待援,而援军则采取东西夹击或南北夹击的方式来解围。结果往往是:固守的一方没能守住,来援的部队又被阻击,最后甚至自己也被包围。黄维兵团就走上了这条老路。
黄维在11月8日接到救援命令后,率12兵团从驻马店、确山一带拼命北上。一路上,他携带大量重武器,还要跨河、走崎岖道路,更不断受到解放军地方部队骚扰。能在11月18日赶到蒙城,已是相当不易。但当他到达时,李延年、刘汝明兵团却行动迟缓,没能按时会合,结果黄维孤军突出。很快,黄百韬被全歼的消息传来,徐州的国军处境更加危险。
此时,有人主张干脆放弃徐州,退守淮河。但由于津浦铁路上的宿县已失,徐州的兵力若要撤退,就必须先夺回宿县。于是,国防部命令黄维继续北上,强行攻宿县。黄维手下有人建议暂守蒙城,或转向怀远,依托蚌埠为后方再北进,但这些建议都被否决。结果,黄维硬着头皮渡过涡河,离大部队越来越远,愈加孤立。
11月23日,中野诱敌之计得手,将黄维兵团引过浍河。等他意识到自己被包围时,已来不及了。黄维慌忙下令掉头撤退,却犯了严重错误——没有按照常规把后队变前队,而是全军直接大掉头。此时他的前队正与中野交火,撤退行动被拖延,最终到11月25日,黄维兵团被困在双堆集周围二十多个村庄中。
国军统帅部依旧老一套:黄维固守待援,邱清泉、孙元良自北南下,李延年、刘汝明自南北上,南北夹击,打通津浦路。解放军则用熟悉的办法应对:先集中兵力歼灭固守的黄维,再阻击援军。于是,淮海战役进入关键的第二阶段。
中野投入7个纵队15万人围歼双堆集的黄维兵团;华野则抽调8个纵队在徐州以南构筑防线,阻击邱清泉、孙元良——这就是徐南阻击战;同时,中野二纵和华野六纵加上地方部队,在蚌埠以西阻击李延年、刘汝明——这就是蚌西阻击战。刘伯承形象地总结:“吃一个(歼灭黄维)、夹一个(监视徐州)、看一个(阻击李、刘)。”
“吃一个”是全歼黄维兵团,战斗极为惨烈,也是淮海战役的核心;“夹一个”关系到徐州杜聿明集团,影响第三阶段全局;而“看一个”则常常被轻描淡写。实际上,蚌西阻击战打得同样血腥。
负责“看一个”的主要是陈再道的二纵和王必成的六纵。六纵最早抵达战场,独力承担压力。李延年的部队一度打到距离双堆集仅30公里的龙王庙,刘汝明也逼近到固镇。他们兵力虽不如邱清泉,但数量是解放军的两倍,还装备精良,一度让六纵险象环生。
六纵第一道防线坚守4天后被迫后撤,第二道防线又因敌军两翼迂回而坚持仅3天。退到最后一道防线时,粟裕亲自打电话给王必成,严令“不许后退”,并派出增援部队。这才稳住局势。
王必成是粟裕手下的“铁拳”,自1938年加入新四军后,几乎参加了所有重要战役。他在淮海战役中,先围歼黄百韬,再急赴蚌西阻击,战斗惨烈无比。正因如此,晚年的他并不认同“看一个”这种说法,认为蚌西阻击战的艰苦与重要性,绝非一个“看”字能概括。
这场鲜为人知的战斗低息配资,实际上是淮海战役能否最终胜利的关键支撑之一。
发布于:天津市配查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